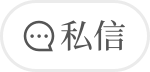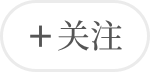五月的祥云湾像被揉碎的万花筒,青石板路浸着阳光,古建筑的飞檐挑着人声鼎沸。我挽着妻子的手穿梭在人潮里,忽然发现,比起雕梁画栋的恢宏,那些高高托起的小小身影,才是这场热闹里最温暖的注脚。
一、戏楼前的“瞭望塔”
川剧变脸的锣鼓敲碎午后的燥热时,古戏楼前早已围得水泄不通。我踮脚望去,只见一片起伏的“人山”中,几座“肉色瞭望塔”格外显眼——穿“我爱你中国”白T恤的小男孩坐在一位父亲右肩头,两条小腿晃啊晃,把父亲的衬衫扯出几道褶皱。那父亲左手圈住孩子的腰,右手时不时替他拂开被汗水黏在额前的头发,自己的脖颈却被晒得通红。“爸爸,他脸变蓝了!”男孩突然指着戏台惊呼,小手拍在父亲头顶,惊飞了停在瓦当上的麻雀。
不远处,穿白丅恤的父亲半蹲着调整肩头的“座椅”,让女儿能看清台上翻转的脸谱,小女孩两手揪住父亲的耳朵,不时地发出欢呼声。还有位年轻的父亲,肩头坐着留着锅盖头的儿子,却笑得眯起眼,仿佛扛着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二、人潮中的“人肉电梯”
小吃街的烟火气里,这样的画面更显温馨。卖糖画的摊位前,一个胖墩墩的男孩扒在父亲肩头,肉乎乎的小手正指着转盘上的龙形图案。父亲踮着脚配合他的视线,脖子仰得老高,汗珠顺着下巴砸在摊位木板上。“爸爸快看,是金色的!”男孩拍着父亲的脸,父亲却只顾着用手掌护住孩子的后腰,生怕他摔下来。
路过画舫码头时,看见一位父亲半跪着,让女儿踩着自己的膝盖爬上肩头。小姑娘刚站稳,就指着湖面惊呼:“大船!大船!”父亲笑着起身,一手托住孩子的臀,一手拎着她的小皮鞋——原来怕鞋子掉进水里,早早就脱下来攥在了手里。阳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,父亲的背影像座拱桥,托起孩子眼中的碧波画舫。
三、时光里的“传承仪式”
人群中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每到农村唱大戏,父亲总会让我骑上他的肩头,那时我总以为,父亲的肩膀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,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记得我女儿小时候,也曾把她架在肩头穿过部队家属院,穿过文化路的大街小巷。此刻看着这些忙碌的父亲们,忽然懂了这肩头上的“仪式”——不是简单的托举,而是把孩子的视野举过自己的人生,是用脊梁搭建的瞭望台,让稚嫩的眼睛先于脚步,触碰到更辽阔的天地。
穿“我爱你中国”T恤的男孩终于等到变脸艺人走到台前,他挥舞着小国旗喊:“叔叔,变红色!”艺人笑着转身,一张绣着金色祥龙的红脸谱在阳光下展开。男孩尖叫着拍掌,父亲却在这时轻轻替他摘下水杯帽,往他额头贴了片湿巾——原来在托举的同时,他始终留意着孩子的冷热饥饱。
暮色漫上飞檐时,我们往出口走。路过戏楼,看见那些父亲们陆续放下肩头的孩子,有的揉着脖子,有的捶着腰,却仍笑着听孩子们叽叽喳喳复述看到的精彩。那个穿白T恤的男孩趴在父亲耳边说了句什么,父亲忽然笑出声,抬手揉乱他的头发。路灯亮起时,我看见男孩的小手勾住父亲的小拇指,而父亲的另一只手,还牢牢护在他后背。
原来父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,而是把孩子举过头顶时的稳稳托住,是汗流浃背时仍保持的微笑,是肩膀发酸却不肯放下的坚持。在祥云湾的人潮里,这些高高托起的小小身影,是比古建筑更永恒的风景,是比川剧变脸更动人的“非遗”——那是血脉里代代相传的温柔,是如山般沉默却永远坚实的依靠。